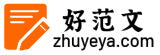《日出》通常被称为社会悲剧。曹禺以陈白露的休息室与翠喜的卧房作为舞台场景,分别连接两类社会生活;通过方达生寻找小东西,来展示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生活苦难。翠喜为生活所迫,小东西终于逃不过金八的魔爪,只能悬梁自尽。曹禺为了刻画这类人的生活,曾冒着危险深入此中观察、了解,并且发现像翠喜一样的人有着金子般的心。第三幕浸透着剧作家的辛酸与愤怒抗议,是全剧的有机统一的一部分,是深化戏剧主题的必须。喧嚣嘈杂的地狱充满着骚动不安,这个社会从上层倒下层全部腐烂、解体了。剧本还安排了一个不出场的人物金八,达到了对社会揭露的深度。
曹禺将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至于金钱统治、人欲横流的社会来考察。曹禺说《日出》没有主角,但陈白露毕竟处于舞台中心,陈白露的悲剧是他内心两个自我冲突的悲剧。这一内心悲剧性冲突搭起了《日出》戏剧冲突的基本骨架。
陈白露曾是“天真可喜的女孩子”,但是灯红酒绿的刺激,锈蚀了她纯洁的灵魂,以致她与诗人的愈合以分手而告终。她再次投入金丝笼而无力飞翔。她拒绝方达生的挽救,似乎玩世不恭、傲慢自负,又不由自主的流露了心灵的颤抖。她为出卖自己的美丽与青春,断送人生希望而痛苦。在方达生面前,她发现自己的“孩子时代”,也发现了自己的悲剧。人生道路与命运的抉择又一次摆在她的面前。在第一幕中,她与方达生谈话,赞美洁白的霜,呼唤自己少女时代的名字;她挺身而出,怒斥黑三,救下小东西;她欢呼太阳,欢呼春天,读起心爱的“日出”诗。“旧我”——她内心中人的要求、意志,要突破“新我”顽强的表现。第三幕,陈白露尽管没有出场,但翠喜、小东西的遭遇同陈白露的命运遥相呼应,并且这一幕的直接结果导致陈白露的希望与追求落空。因此第四幕一开始,陈白露已是泪流满面,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与痛苦。她从小东西的遭遇终于明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,她痛苦的回忆着昔日的悲剧,诗人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她的眼前。而历史的隐痛同时也被血淋淋的挑出来。她明白寄生的腐朽生活使她陷入深坑无力自拔,而她又不愿意再过这种出卖心灵与肉体的生活,她终于断然结束了个人的生命。她的心灵悲剧是黑暗社会对人的精神要求的毁灭。陈白露怀着向往“日出”之心而死,反映了她内心对人的自身价值的憧憬。
“我没有故意害过人,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故意抢到自己的碗里,我同他们一样爱钱,想法子弄钱,但我弄到的是我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。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,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,因为我牺牲过自己。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可怜的义务,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!”这是做了交际花的陈白露对他少年时代朋友方达生的申辩。这个辩词貌似倔强,却又是何等软弱,又包含着多少痛苦?在这里深刻的反映了陈白露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,以及她的精神危机。一个曾经有着美妙青春、漂亮、能干的少女,一旦堕入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里,就不得自拔。她明知太阳出来,但又清醒的看到太阳不属于她。打的黑暗势力吞噬了她,她精神崩溃了,结束了年轻的生命。
《日出》新的“横断面式”的剧作结构恰恰是作者出于剧情以及题材本身需要而采用的,这种结构是此剧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,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开创价值。曹禺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些有肉的人物,真像是那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个摄魂者。在题材的选择、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,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,不尚热闹,却精于调遣,能透视舞台的效果。
结构的方法总是对象的适应性产物,从来没有固定的格式。它的构架特点,即以陈白露的休息厅为活动地点,展开上层腐败混乱的社会相。同以翠喜所在的宝和下处为活动地点,展开下层第地狱般的生活对照起来,交织起来。加上一个第三幕,即宝和下处的妓女生活片段,这就加强了作者对现实的抨击力量,加深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概括。显示了曹禺富于艺术胆识和打破陈规、超越自我的创新力。曹禺说他是在“试探一次新路”,这试探,并非只是结构上的,二是探索现实生活做更为广泛的概括。
如果说在《雷雨》中,作者还对充满斗争的残酷和血腥的现实有一种困惑,以那样的社会真实相太复杂,“没有能力形容它的真实相”,未免带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。那么《日出》中他比较明确表达了“自己的哲学”,不再是不可捉摸的“宇宙里的斗争”,二是对人吃人的社会真实相粗略的概括。他说“目前的社会固是黑暗,人心却未必堕落到若何田地,症结还归在整个制度”。
方达生不能代表《日出》中的理想人物,正如陈白露不是《日出》中健全的女性。这一男一女,一个傻气,一个聪明,都是所谓的“有心人”。他们痛心疾首地厌恶那腐恶的环境,都想有所反抗,然而陈白露气馁了。一个久经风尘的女人,断然的跟着黑夜走了。方达生——那么一个永在“心里头”活的书**,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,整日的思索斟酌、长吁短叹。末尾,听见大众严肃工作的声音忽然欢呼起来,空泛的嚷着要做些事情,以为自己的了救星,是多么可笑又可怜的举动。他说过他要“感化”陈白露,陈白露笑了笑没有理他。现在他的想象又燃烧起来,他要做点事业,要改造世界,独力把太阳唤起来。倒是陈白露看得穿,她知道太阳会升起来,黑暗也会留在后面,然而她清楚“太阳不是我们的”。长叹一声便“睡”了。这个“我们”,有陈白露,有方达生,包含了《日出》里所有的在场人物。描绘的不是日出以前的事情,有了阳光的人们始终藏在背影后,没有明显的走在前面。曹禺写出了希望,一种令人兴奋的希望。他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,但也只是暗示着。
《日出》是生活场景的展示,众多的剧中人相互交往,而不是几个角色围绕着一个中心事件展开。陈白露的中心冲突也不同于《雷雨》中剧中人与剧中人的正面交锋。他把诗意的发现和现实的揭示有机的熔铸起来。它不仅仅把那个“漆黑的世界”图画描绘出来,就他对那个社会的揭露来看,它的污秽、混乱,还使人感到那发散着腐尸的恶浊气息的社会,却是一座人间的地狱。但是《日出》的迷人之处却是在“漆黑的世界”里又透露漫天大红的天色;在冷酷中,蕴藏着温热;在地狱里,有着金子的闪光;在腐尸臭气下,潜藏着牵动人心的诗意的力量。《日出》的现实主义又注入了新的血液,融入了作者理想的温暖和浪漫的诗情。“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,取了乐了走了,可是谁心里的委屈谁知道,半夜里想想,那个不是父母养活的,那个小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?那个大了不是生儿育女,在家里当老的?哼,都是人,谁生下来就这么贱骨头,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”是啊,“都是人”,谁愿意堕入这非人的境地?这真实的心灵自由,是对罪恶社会制度的控诉。对人的价值、人的精神遭到摧残和蹂躏的无比愤慨。使作者未恢复人和发现人的价值而进行斗争。他以为,像翠喜这些“可怜的动物”,她们的心灵一样,不能不使人想——究竟是什么毁灭着她们的美。
所以说,诗意的灵魂,渗透在戏剧结构的血肉之中。处处是充满诗意的对比,激扬着愤慨的深刻,同犹如发现新大陆那样对美丽心灵的揭示和美的泯灭的悲剧,是那样交织着激荡着。作者崇高的人道主义在剧本里汇成对旧世界强烈的控诉。在《日出》中,他不是写陈白露、翠喜堕落的悲剧,而是她们这样一些纯洁善良的女人是怎样走进悲剧深渊的,作者穷追猛打的正是那个社会制度,作者写的是诗意的真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