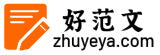春天快要过去啦,它走得很急,我也有点儿急。
去年的这个时候,每到周末陪女儿上辅导班,一送她进去,我便跑到公园里散步,看花。
我看过那棵日本早樱肆意泼洒的样子。巨大的花叶蓬蓬然、灿灿然,如盖一般,遮住了大半条道。花瓣儿簇成满树的雪白,在微风中颤动着一团又一团笑意。可惜她的花期极其短暂,一周前去看,初盛,一周后去看,无踪。一阵风便能将她们全部打包带走似的。这或者就是她可人之处。因其短暂,所以美好。那么微小,那么柔嫩,经不起风吹,经不起雨打,没过多久,自己怯怯地主动萎去。
我还看过海棠。在那座公园里,海棠的种类有很多,我只认得两种,一个是垂丝海棠半掩半落,另一个是西府海棠艳若红妆。她们开得比那株日本早樱要晚点儿。海棠花的枝条遒劲有力,如同水墨画上画的那样,节枝参差,错落斑驳。叶子油绿油绿的,衬托着或浅粉或艳红的花朵,好像随意入镜便是一幅现成的盆景,精巧别致,深得朕心。
梨花似乎更晚一些,她比早樱更加雪白,花瓣朵朵分明,五瓣儿还是六瓣儿,娇俏地围成一圈儿,中间蹙起几根嫩红色的蕊。看到梨花,就会想起那首歌:忘不了故乡,年年梨花放,染白了山冈,我的小村庄。妈妈坐在梨树下,纺车嗡嗡响,我爬上梨树枝,闻那梨花香。于是梨花就成了口中哼唱的歌谣,满满的画面,满满的回忆。我喜欢梨花,她总是安安静静的,和那首歌一样,唱着唱着就想入睡,看着看着,也想入睡。
小的时候,在老家的院子里看到过桐花。淡紫色渐变的肥腻腻的花瓣儿,像用什么雕刻出来的,润润的,身上还扑着一层很细很细的绒毛,散发着淡淡的甜味儿。我和姐姐满院子疯跑,捡掉落在地上的桐花。掉下来的桐花的底托有点儿焦黄,但娇艳仍在,绒毛仍在,甜甜的味儿仍在。轻轻捏着底托儿对着太阳转动,就连太阳都变成花瓣儿的样子啦。不过最常干的是拿着手指头往里面捅着玩儿,把花蕊深处的花粉一点点粘出来。花粉粘到手指头上,不太好洗,浅黄色的印痕几天才会洗掉。
迎春花和连翘花我一直分不清。看到路边那一大堆一大堆的黄色的花我都管她叫迎春花。长长的枝条上缀满了嫩黄,让人忍不住很想去折下几根来,编织成一个……花环?还是算了,有花堪折直须折,那是属于诗句的,不是属于现实的。在成年人的世界里,即使再喜欢,也只是看看罢了,看她生长得好好儿的,迎着阳光笑得那么灿烂,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。
在不知名的野外,我还看到许多不知名的花花草草。草乱蓬蓬的,带着露水,星星点点的小花们就藏在草们的身边,一个个使劲儿向上露着头,仿佛在找蓝蓝的天空——尽管个头儿矮小,也有仰望天空的梦想。鞋子被露水打湿了,那是因为俯下身子拍那些小花造成的。当我俯拍她们的时候,绿草是她们的背景;我趴在比她们低的地方,从下向上拍她们的时候,蓝天便是她们的背景啦。她们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用意,小脸儿仰得更高,身子挺得更直,满脸兴奋与得意。
掐掐指头,蔷薇也快开了吧?家附近有条小路,路两边的小区围栏全都是蔷薇。等她们开放了,那条小路就变成名副其实的花径啦。蔷薇可是一点儿也不会害羞,她们可是成群结队的,赶趟儿似的开啊开,浅粉的,深粉的,大红的,深浅不一的,非要把长长的围栏全部开个遍,让路过的人不舍得走,就这么大范儿。
小区门外,左侧有一株桃花,右侧有一株杏花。好像都快开了?还是好像刚刚开过?我还真没怎么留意过。可能旁边那两尊石头狮子知道吧。
这么一算,春天的花儿还真挺多。
听说明天或者后天降温有雨,也不知道风雨过后那些花儿们是绿肥红瘦了呢,还是开得更欢了呢。好吧,那我不急了,就等着吧,等着看这场风雨之后的花儿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