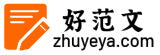“未免”应是“未必”
辛南生
余秋雨先生在《一个王朝的背影》一文中,谈及亲政不久、稚气未脱的少年郎康熙竟然眼盯着两个庞然大物——权倾一世的鳌拜及远处边陲拥兵自重的吴三桂。他说:“平心而论,对于这样与自己的祖辈、父辈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政治势力,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免下得了决心去动手,但康熙却向他们,也向自己挑战了……”
上文中“未免”一词应该改为“未必”。“未免”释义之一是“免不了”的意思。“未免下得了决心”,等于说“免不了下得了决心”。作者这段话的原意本来是想把康熙与即便是一代雄主的人物作对比,以显示康熙的果敢与坚强。如果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“免不了”下得了决心去动手的话,英雄所见略同,那就失去了对比的意义,岂不和原本想要突出年轻有为的康熙的气魄与业绩的意图相违背?
“未必”的意思相当于口语“不一定”,是表示否定的较委婉的说法。如唐·陆龟蒙《吴宫怀古》:“吴王事事堪亡国,未必西施胜六宫。”就是说是吴王的亡国并不是由于西施的盅惑而是由于他自己的恶行,把上文句中的“未免”改为“未必”则原句便成了“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不一定敢采取的行动,康熙却毅然采取了并获得了成功,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康熙非凡的眼光和才干。”
“朵而”不是“朵尔”
尤敦明
常看电视的人都熟知“朵而”胶囊这则广告,然而如果不看画面,就弄不清这种养颜胶囊的名称究竟是哪两个字,因为画面音是duǒ’ěr(朵尔)。“朵而”应该读作duǒér。“朵”是上声字。大家知道两个上声字相连,前一个字声调变得像阳平duǒ,但上声字和其他声调字相连则读音不是变得像阳平。“而”的声调是阳平,所以“朵”不可能变成阳平,像广告中的读音,那只有把“而”(ér)改成“尔”(ěr)才行。人们对两个上声相连的词常常读不好,这使我连想到一个常用词“偶尔”(ǒuěr)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很多人读ǒuér,也许因为不熟悉“尔”的声调,也可能是读不好两个上声相连的变调。这种胶囊的名字“朵而”正好避开了上声字相连的变调,为什么一定要让它来一个变调呢?眼下年轻的姑娘们口头出现的已经都是duǒěr(朵尔)了。这则广告画面不错,如果把语音纠正一下,一定会收到更佳的广告效果。
谈“坐”和“座”
中文实在很难,其中造成困惑的原因之一,是本只一个字,根据社会需要发展演变,又造出另一个字来分担它的某些用途。于是,最早是一个字,后来两个通用,再后则分工明确不再互代。不过,用者有说是旧用,有讲是新说,则形成笔墨官司了。立法会普分“身分”和“身份”争得不亦乐乎;“坐”和“座”把人弄糊涂了,也常发生。
“坐”是古字,原本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,当然无所谓用对用错。现代汉语则增加了“座”,分工大略是凡是动词,则用“坐”,指臀部着物之动作及其引申,坐下、坐堂、坐享其成、坐井观天、坐吃册空、坐冷板凳、坐失良机、坐言起行……都应该用“坐”字。“座”是用于名词及发展出以名词作量词的时候常用,如满座、对号入座、第三座、一座楼、两座山、五座塔……这些都无大争论。
“坐位”和“座位”;“坐落”和“座落”这两组词都能见到,这是这两个字已有明确分工后的特别例子。“座位”和“坐落”都属组语法上的联合结构,当然正确;“坐位”没大问题,“座落”是主谓结构,只算可勉强说通。
“毋”和“母”
“毋”和“母”字体相近,尤其手写时不注意,常写错误用。两字在内地会少出些错误(不是不出错),因为普通话的读音区别很大,“毋”wu的第二声,“母”读作mu的第三声;但是粤语却都可读“无”。
“母”字当然人人明白,母亲、母体、母系、母语、母校、母牛、母羊、母鸡……注意写字时不要把两点连成一撇就是了,“毋”是个副词,意思表示禁止或劝阻、“不要”,如“毋庸”是无须;“毋宁”是不如;“毋望”是不冀希望;“毋妄言”是不必狂妄指责……
粤语的“毋”、“母”同音,这在读书时便更需要小心避免误解。清代的《广谈助》记载了一则笑话,讲一位总读别字的先生,大家同他半开玩笑地说,要惩罚他做狗。这位先生一本正经地回答:做狗可以,但不做公狗,要做母狗。人们大惑不解,这位仁兄说道:“孔夫子《论语》中说,‘临财母狗得,临难母狗免。’你看,孔圣人都说,临到发财之时,是母狗得到,遇到灾难之际,是母狗才可幸免嘛!”大家笑得前仰后合,原来这别字先生又读了别字,《论语》原文是“临财毋苟得,临难毋苟免”,意思是面临财宝时不可求取能得就得,面临灾难时不能侥幸求得幸免。这先生将“毋苟”读成“母苟”,再理解成“母狗”,难怪他要求一定要做只母狗啊!
“洲”和“州”
“洲”和“州”写法相近,读音相同,又都可做地名用,但是两者仍有明显区别,不可随意加多或省略三点水。
“洲”有水字偏旁,是水中之地的意思。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,第一篇《关雎》有个脍炙人口的名句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,此“洲”亦即水中绿地;现在世界上的亚洲、欧洲、非洲、美洲……的“洲”仍然是水中大陆的意思。古人曾把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,说成“三山六水一分田”,他们认为山占了百分之三十,水占了百分之六十,田地才占百分之十。比例虽不能说十分精确,但是,古人测算的水多田少是正确的。
因此,陆地(洲)是被水包围着,才有了上述的欧、亚、非、美洲说法。
“州”则本是古代行政区域名,比如二千多年前的汉代前后,全国有过九州或十三州记载,“州”大体上同现在的“省”差不多。因此,现在我们自己称中国还有“神州”、“九州”说法。
不过,要注意中国的行政“州”在元、明、清代时,大大缩小,差不多相当于“县”了。所以至今有些“县”还同时叫做“州”,比如旧时沧州亦沧县;通州亦即通县;涿州即涿县。近代“州”已变小了。
明白了“洲、州”区别,那么在书写神州、欧洲、俄亥俄州、五洲四海、只许州官放火……时,就不会写错了。
“丏”与“丐”
标题上写的这两个字,读音完全不同,意思更大相径庭。
“丏”字粤语和普通话读“免”音,是遮蔽、看不见的意思。但是,因为“丏”字现在很少用到,除了读古文或是有时人名用到之外,这个字正在现代汉语中渐渐消亡。而“丐”字大家熟悉,人人皆知是“乞丐”之“丐”了。
两字写法近似,但是绝对不同,不可马虎,要小心区分。中学课本中有篇《白马湖之冬》,作者是夏丏尊。
当代青年对夏丏尊先生知之不多了,他是已故现代作家、教育家兼翻译家,在三四十年代,他曾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,他和其他文化名人一起,不仅亲自教学,还从事写作,作品颇多。夏先生还亲自办书店(开明书店),办《中学生》杂志。更把外国关于教育方面的著作亲自翻译介绍到中国来,著名的《爱的教育》是他译著的代表。
有位学生称《白马湖之冬》的作者夏丏尊为夏“丐”尊,这是个不求甚解的误会。
前文我说了这两字解释完全不同,虽然“丏”字在消亡中,但人名中偶尔还能遇到。以老前辈作家夏丏尊的名字来说,他用了“丏尊”,应是谦称“遮蔽尊崇”或“看不到尊严”的含义。若变成“丐尊”,是“乞丐尊敬”之意,这老作家岂非成了乞丐头子啦?
“副”与“幅”
标题上这两个字,“副”在粤语和普通话中,都读作“富”音;“幅”在两种语言中又都读成“福”音。
它们的意思不同,而且,都可做量词,写用时要注意区分。
“副”可儿解作居于第二位,比如,副官、副总统、副教授、副班长、副食品(主要的米面主食以外的菜肉佐料之类)等;还可解作辅助的,比如副本、副刊、轮船上的大副、二副;它又可解作附带的,比如副业、副产品、副作用等。它有个作“符合”解释的词义要特别注意,例如成语“名副其实”和“名不副实”,“副”必须讲成“符合”,却不可写成“名符其实”和“名不符实”。
“副”字作量词时,有两大类用法:一个是用于某些成套的东西,比如全副武装、一副对联。在说“手套”、“筷子”等物时,可说“一双”,也可称“一副”;另一个用法是指面部表情,如一副笑脸,一副庄严面孔等。
“幅”本指丝绸布匹的宽度,如幅面、单幅、双幅、宽幅等。从这引申出其他的宽度也常用“幅”,比如幅度、幅员(领土面积。“幅”指宽窄,“员”指周长)、振幅等。它也可作量词,但注意不同于“副”,它可做布匹量词,如“做个床单要两幅布”。说“一幅画”是正确的,等同于“一张画”,但“一副对联”则不用“一幅对联”则不用“幅”,中文真难啊!